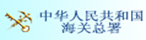观点丨“后《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法制进展与执法完善
自2016年修订以来,《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与时俱进就面临着法制完善、机构改革和行政转型带来的挑战,这一是指食品安全立法工作需通过条例修订和规章配套来进一步促进法制在数量规模和质量升级上的完善,尤其是通过考虑专家建议和行业反馈来提升食品安全法律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二是指机构改革后,内部规章制定权的分配、既有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审查、相关法律法规的协同和综合执法等加剧的法制工作压力;三是在“放管服”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最严”的要求和行业合规创新发展的平衡。
鉴上,最终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回应性的制度安排,包括进一步细化《食品安全法》中的义务要求,尤其是加强企业主体责任,进而提高该法律要求的可操作性;针对实践法治中的突出问题,在行政法规这一顶层设计中给出统一性的规范要求,如应对保健食品销售中的虚假宣传;多管齐下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例如,强化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规范食品安全教育等基础制度、完善地方和企业等标准管理工作、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员和明确检验补充方法,等等。对于上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结合当下的法治实践,未来食品安全法制的发展和执法的提升,可以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
来强化主体责任
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强化了生产经营企业的主体责任,这不仅体现在要求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内部的供应商管理、进货和出场检验、生产经营控制、食品安全自查等管理制度,而且也从能力建设和责任设定方面明确了如何落实质量授权、培训考核、处罚到人的规定。与此同时,条例也针对委托生产、食品添加剂管理等突出问题明确了相关主体的义务与责任。
比较而言,上述制度的有效落实还有赖于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将外在的法律要求转变为内部的合规管理。实践中,在违规成本日益加剧,生产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信用管理的当下,合规也已成为生产经营者承诺保障食品安全、赢得消费者信赖的重要途径。对于这一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的转变,体现“最严”要求的法律制度依旧发挥着外部的制约作用,即借助义务和责任的设定来威慑企业采取合规管理。在此基础上,对于企业的合规自觉,主管部门也可以从指导、激励等方面来营造有利于企业合规管理的监管环境。也就是说,在法律法规等“硬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指南、最佳实践等“软法”来细化企业做好合规工作的细则要求。在这个方面,行业协会也可以借助自律性的指南等来督促企业的合规工作,而这也体现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原则性要求。
此外,食品生产经营者也是重要的社会共治角色,因为他们所具有的市场力量可以通过联盟来抵制前端供应商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在强化惩戒违法行为的同时,对于生产经营者通过制度创新、合规管理所促进的食品安全工作,尤其是突出贡献,也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事实上,《食品安全法》所引入的“尽职免责”制度,本身便是有利的合规奖励工具,即在一定的场景下针对落实了进货查验的食品经营者免于食品安全标准方面的违规处罚。
从“一刀切”转向回应性的“一刀一刀切”
要促进上述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合规管理和发挥他们源于市场的协同治理效果,政府的监管也需要从“一刀切”的模式转向回应性的“一刀一刀切”。这一方面是指食品安全执法应突出打击具有“主观恶意”的违法行为。在这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法》在设定行政处罚时,本身也针对情节严重的情形加重了处罚。对此,《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明确何为情节严重时也纳入了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主观方面。值得一提到的是,在架构“处罚到人”这一制度时,追究个人责任时考虑其主观故意也是题中之意。例如,根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印发关于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到人的规定的通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违法行为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主管人员”这一定义,暗含了考虑主管人员“授意”、“纵容”的主观故意。
另一方面,风险管理是食品安全工作的原则性要求,也就是说,监管的回应性可以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事实上,面对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些地方的监管实务已经开始依据客观的风险程度来设定分类监管的要求,进而在风险预防的同时促进监管工作的高效性和便民性。例如,《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实施指南》明确了已取得风险等级较高经营项目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堂,从事风险等级相同或较低的经营项目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可以不增加相关经营项目。再例如,《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快推进食品经营许可改革工作的通知》便要求对监管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要加强调查研究,适时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状况和关键风险点评估,以包容审慎为原则,探索制定有针对性的许可和日常监管要求、措施,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一刀一刀切”式的回应性执法意在合理归责、风险管理等原则导向下提高执法的灵活性,但其与选择性执法、同案不同罚的恣意性不同。对于后者,既有的法治实践表明:在自上而下的制度落实中,如果国家层面的规则不明确,地方立法、执法中就容易出现扩张或限缩的解释,进而加剧差异化执法带来的不公平性。对此,主管部门抑或行业协会结合调查研究,出台意在细化法律规则要求、反映行业合理诉求的指南可以成为企业的合规导向,并促进地方执法的统一性。例如,对于执法和司法中依旧存有争议的“标签瑕疵”,便可以借助既有的法治实务和案例,通过总结、归纳适用场景来增进对于该定义具体所指的共识。
从单项制度的可操作性到
多项制度的组合效应
《食品安全法》根据不同的原则要求和多样的主体、环节、产品等设定了诸多的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一个作用是制度方面的“推陈出新”。对此,除了通过细化来提升单项制度的可操作性,也可以通过对关联制度的组合适用来提升食品安全工作。事实上,“组合拳”本身便是《食品安全法》在制度架构时所考虑的因素,尤其是通过综合应用金钱罚、自由罚、声誉罚等来处罚和威慑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对于“后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时期的法制(治)完善,结合上文论述的企业合规发展和政府执法的回应性改进,可以进一步借助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评估和问题导向的调查研究,来发现法律制度组合适用中的挑战,进而依托于后续的规章制定、指南编写、案例指导来针对性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例如,对于履行主体责任,《食品安全法》第136条“尽职免责”为经营者提供了合规免责的制度设计;同样的,对于“屡罚不改”的多次违法行为,第134条“三振出局”的制度设计则针对性地加重了对当事人的处罚。然而,就两项制度的衔接而言,尚不明确的是:第136条情形下的“没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是在“免于处罚”的前提下发生的,而这究竟是风险管理行为还是行政处罚?如果是后者,则会使得经营者因为累计三次的处罚而遭致停产停业的加重处罚。显然,这无法体现“三振出局”制度在设计时意在应对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的初衷。而第136条和第134条自身在内容上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加剧了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如“进货查验等”义务履行中等内等外的不同释义,“责令停产停业”在强制与否和期限多少方面出现的地方适用差异。鉴上,通过后续的法制完善和法治提升来应对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彰显食品安全立法的“严者更严,宽者更宽,刚柔并济而不失法度。”